马蹄
书名:庄子本章字数:1676
【原文】
马,蹄可以践霜雪,毛可以御风寒。龁草饮水,翘足而陆,此马之真性也。虽有义台路寝,无所用之。及至伯乐,曰:“我善治马。”烧之,剔之,刻之,雒之,连之以羁馽,编之以皂栈,马之死者十二三矣;饥之,渴之,驰之,骤之,整之,齐之,前有橛饰之患,而后有鞭策之威,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。陶者曰:“我善治埴。圆者中规,方者中矩。”匠人曰:“我善治木,曲者中钩,直者应绳。”夫埴、木之性,岂欲中规矩钩绳哉?然且...
下载奇迹小说APP,永久免费阅读全文
立即下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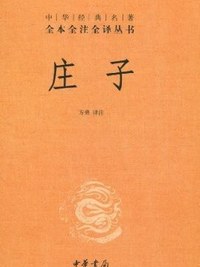
庄子
作者: (战国)庄周共0章
倒序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