胠箧(1)
书名:庄子本章字数:1787
【原文】
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,则必摄缄縢,固扃,此世俗之所谓知也。然而巨盗至,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,唯恐缄縢扃之不固也。然则乡之所谓知者,不乃为大盗积者也?
故尝试论之:世俗之所谓知者,有不为大盗积者乎?所谓圣者,有不为大盗守者乎?何以知其然邪?昔者齐国邻邑相望,鸡狗之音相闻,罔罟之所布,耒耨之所刺,方二千余里。阖四竟之内,所以立宗庙社稷,治邑屋州闾乡曲者,曷尝不法圣人哉!然而田成子一旦杀...
下载奇迹小说APP,永久免费阅读全文
立即下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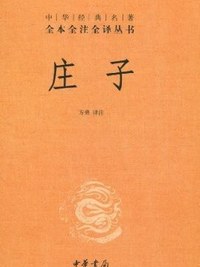
庄子
作者: (战国)庄周共0章
倒序
